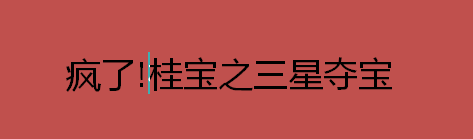魂报素材号代投稿声明:为方便读者和投稿者,魂报一直开放有【魂报素材号】代投稿服务,文章仅代表投稿人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和态度。
第一个世界里,枝江刚建成不久,从东走到西只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万物的运转都是那么小心翼翼。郊外,白色的树木遮天蔽日,人们把树片片砍倒,白色的巨像在触地的一瞬间化为了千万白色的蝴蝶,翅膀上闪烁着初升的淡紫色太阳的光芒。水泥从地下缓缓升起,小心地相互啮合着。
 【资料图】
【资料图】
最初,人们不好定义他们自己是什么,或是枝江是什么。便说:“这座水泥之城以外混沌错综且疯狂。以内是常态。”
# # #
我醒来时,看了眼手表,凌晨五点左右。
我先盯着天花板上的静止的镀铬风扇核心看。大脑好像在旋转,被搅得生疼。我索性闭住眼睛,但那种黑暗又将我死死抓住让我喘不过气来。黑暗中,匕首再次插入我的胸口,血液喷涌而出,粘在了牛角面包上。
于是我再次睁开眼,翻了个身,看到了蓝色的床帘背后,正在微微发出光。短暂的寂静,鸟鸣声,但最后又回到了平和之中。平和。我想起了我已经放弃的小说,想起了那个疯子。房间中,既不是所谓明亮,又不是黑暗,而是淡色的秋天的树叶飘落至水洼之中的那种朦胧与迷离。这个房间中无论红的黑的橙的蓝的都一并褪去色彩化为遗忘的白。我又试着闭住眼睛,但大脑的嘈杂想必已经完全赶走了我仅剩下的一丝睡意,便索性小心地翻身起来。我赤着脚走到电脑旁,路过餐桌时看了一眼,吃了一半的可颂还放在盘中,和枯萎的草木一样变得干脆。
(血溅在面包上,疯子如是说。)
我打开电脑,幽灵般的荧屏再次亮起。文件夹弹出,里面那篇被我搁置了两周的讲述东北往事的小说正像因无人认领而弃于街边的死尸一样孤独且无望。我想了想,仍然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语句,索性不写了,就把残稿抛在那里。相反,前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奇异、超现实的事情又重新回荡在我脑中。它多少是有些价值的,又或是足以吸引人们注意的,写下它来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我闭上眼睛,想要寻找一个明确的开头,却发觉有关那件事的一切都和达利的软表一样软绵绵瘫在一起,相互纠葛无法分开。
(好的,一切最初的开始。我所写的故事,都是曾发生在这个工厂里的。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工厂。)
我敲下了第一个字。电脑显示时间是凌晨五点十一分。
凌晨五点十一分的枝江的街道两侧,想必已经有店铺亮起了灯。
凌晨五点十一分,枝江市在复苏。
# # #
第二个世界里,枝江市开始延展,一条河流从西流到了东,在星河下的虚空无尽坠落。人们挖开了柔软的,似大脑褶皱般的土壤,发现他们的世界不过是建立在一片凝固着的灰色的大海上。人们放下了木桶,从枝江市地底下打捞出来了无数珍宝:怪异的歌曲、写满畸形文字的纸张、风格迥异的视频、千奇百怪的棉质品....
人们盯着这些被他们从枝江市地底下放出来的神秘物件,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思来想去,便把这些东西放到了水泥屋中。而对于他们来说,从凝固的大海到水泥隔间,不过凝望到的都是灰色而已。但那些幻想之物将亡,在它们死去的过程中,枝江市的通向灰色的大海的井越来越多。
那片海被人们称作意识海。
# # #
年轻人打了两下火,没打着,餐馆暖黄的灯光下叼着烟的他略显出几分焦灼的疲态。接着是第三下,香烟上染上了火星。我和他曾是高中同学,但已经有了五年多没再见,他的脸变得愈发陌生。不可置否,我们在变老,在变得和生活的肌肤一样失去了活性,只剩下苦涩在那岁月的鸿沟中流转。
“平常就一份西式晚餐,面包配点腊肠,算不上好的。每天晚上七点……我看看……七点半给他送过去。记得用食堂里的餐盘,我有个干净的,你以后用那个给他送。”他说,但光叼着烟,声音有点含糊了。
我撇了眼靠在墙上的铁质托盘,点点头,说:“好。医院的人多会来?”
“这事是我们工地上的,你就不要操心了。这次见面不易,你要明白。”他顿了顿,餐厅里的气氛又略显尴尬,“没事嘛,遇到瓶颈就该多出来走走,和人聊聊天什么的。”
他拍了拍我的肩,我只是点头,不想再听这个人的那些残破的话语。低头看了眼手表,一圈一圈绕着转的指针像是缓缓逼近的柳叶刀,将人的一生缓缓计量着,划分着,切割着,距离七点半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说了句什么,我没注意听,但我仍是默默点点头,虽然心底对这种应付很是抵触。然后柔软的冰被丢进闪着微红的酒中。脑子扔进福尔马林,我这么想。枝江市在腐烂。
我拿起玻璃杯往嘴边凑了凑,迟疑着要不要喝下去。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这个年轻人,他已经放下了烟,酒也喝了点。餐厅的玻璃烟灰缸里撒上了一层灰白色的烟灰。
“出来走走,对,也是,让我过来照看个疯子。”我喝了一口酒,嗓子中火辣辣的。我自然明白他废了那么多心思把我拉到这来是要干什么。
“你话也不能这么说。看厂子的人也就今天晚上有点事不在,你陪他一夜就行了。况且这里马上就要拆了。”
我想,也是,和疯子聊聊天或许挺不错的。我靠住椅背,透过窗玻璃看着外面的世界。夏天病得很重,树叶正在病变成黄色,像病态的肺泡,失去活力,脆弱易碎,它的骨骼褪去了原有泛着淡绿的略带韧性的枝干,愈发坚硬易折。西边黄昏,红色,夏天在咳血了。它挺不过几周了。
“先走吧。”我说,“咱们先往厂子那边走。”
他说:“时间还早,再喝几口。”
我摇摇头。
“我想见见他。或是……只要有人能和我聊聊天就好。”
“行吧,我就知道该找你来,咱俩上学时你一直都蛮怪的,不是?哈,挺有玩艺术的那种感觉。你等等,我去把那家伙要的买上。”
于是,十分钟后,我们向东走去,枝江市的街道纵横交织,仿佛会一直延伸到世界的边缘,但或许,每条道路的终点都是世界终末的边缘。
灰色的破旧厂房透过雾蒙蒙的空气,暴露在我们视野中。它蜷缩在那里,好像这个北方小城工业化浪潮后留在历史的沙滩上的一具骸骨。而在几天后,那里将会在挖掘机和起重机的联合爆破下化为瓦砾。这只是拆移歌舞团的一曲现代化遗忘悲歌而已。
# # #
第三个世界中,枝江市已经无限延展,直抵世界的边缘。更多的灰色水泥屋拔地而起,其中珍藏着从意识海打捞出出来的珍宝也越来越多,就由它们在房间中堆积着,犹如小山。这些幻想与怪异之物不仅仅是枝江市中特殊的唯一了,河流纵横交错,赛博的霓虹映照着原始的古村落,普罗米修斯盗下的火在海沟下熊熊燃烧。人们再一次发现了枝江市的特殊之处——那一个又一个通往意识海的井,正在改变着一切。从井中腾升出的烟雾将河流变成了固态的生活,天也不完全是紫色,太阳开始自由生长,而在那个曾为月亮的天体升起时有一千个羽管风琴一齐奏响。
但是,事情很快就往不可知的方向发展。先是有一天,人们打开了一座水泥屋的门,发现里面涌出的都是意识海的那冰冷的灰色海水。他们曾经打捞上来的东西,都化为了一切的初始——水。
枝江市中的十三位决策者坐在一起,商议了这个事情。最后,他们发现,枝江市的这些外来物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断索取,就一定会有一些在不断消亡,这本是一条冰冷的定律。正当这时,他们突然想到,那么,他们是不是从海中生出的呢?那无数座水泥屋是不是从海中生出的呢?
或是,不如提一个更加逼近终极的问题,整个枝江市是否是从海中生出的呢?
# # #
我们走到时,天已经有点黑了,西边仍存留有仅剩几滴折射下的落日余晖。
过了大门,一条大道延伸出去,将排列在两边的工厂厂房分割,厂子里的东西都搬空了。水泥建筑内的灰暗正在慢慢溢出,与这个黑夜渐渐融为一体,灰黑色的厂房轮廓也被黑色的天空磨没了棱角。大部分都上了锁,有几间门虚掩着,风也吹不动,只是发出沉闷的响。地上有文件,字迹全部模糊了,恐怕是一场大雨后霉菌吃掉了记忆。有报纸,日期写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了,大概九十年代的样子。
“这厂子搁了有多久?”我问。
“少说也有十年二十年了,地皮不清,没办法。”
我们继续走着,每个厂房上的字也大都斑驳,看不清了,分不清是装配车间还是喷漆车间。一地的玻璃碎渣安详而疲惫地瘫倒在地,仿佛曾从路转角的医护室摇摇晃晃走出过。医护室里能看到病床,有支架,点滴还挂在上面,空的青霉素瓶散了一地。我们走过转角,医护室往后是工人剧院,里面的舞台和座椅和喝醉了的人一样烂倒了一片。在继续走,一块歪斜的牌匾闯入眼中,上面斑驳的红漆写下的字上能看清:食堂。
我们停下了脚步,一时间和风一起凝固在这里。
“他就呆在这?多长时间了。”
“自从我们发现起,就一直在这里的了。”
于是他领着我穿过食堂正门,天色暗了下来,建筑内的阴影和黑夜一起沉眠搁浅在这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没有腐烂味,只是颓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厂房一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携式手电筒,开辟出了一道光。
我们排列整齐的餐桌间走着,最后在一张桌前停了下来。
“从正门进,步行十三个桌子后,左转第四个。我们最初就是在这里发现他的,他当时趴在这里睡觉。你最好记住。”
“嗯。”我点点头。
(十三,左转四。)
“手电就留给你了,队里还有点事,我急着赶过去。你只要看好这个破厂子和那个疯子就好了。”
我又死板地点点头。
他把餐盘放在桌上,然后摆上面包和香肠,然后就离开了。我用手电筒灯光四下晃动半天,在瞬间让我看清了周围——大大小小不同的餐盘四下叠垒着。我坐在餐盘对面,等着那个蜗居在这里的疯子。我借着手电筒的光看了一眼手表——半点过五分。我看着这黑暗的一切,感到恐惧慢慢侵噬了我。我感到我手电筒的光逐渐旋转,变成了一把匕首,猛然插入我的心脏,然后抽出,血液犹如火山喷发般涌出。
伴随着心脏的骤然疼痛,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温热的粘液沾满了我的右手。手电筒的光下,依稀可见血红色。我愣了几秒,紧接着张口正欲大叫,但尖叫半途死在了喉咙口。我看到我的对面出现了一个人,他头发长得很长,盘曲纠结在一起,胡子胡乱肆意地长着,面色很黑,身上穿着一套破旧实验服。牛角面包和香肠安然躺在他面前的盘中。
“很高兴遇见你。你是搞文学的,对吧?他和我聊了聊你。”疯子扭过头,看了看年轻人,年轻人点了点头,“很荣幸,很荣幸,我也一直在写些东西。你愿听听吗?”他的声音沙哑而平静,一点不疯疯癫癫。声音在这暗夜中突然腾现,就好像他一样。
胸口的血在手电光下逐渐干涸,但仍然微微地闪着光。难道没有人看到吗?我想。我机械地点点头。一切的发生都太过于突然。
“好。你也知道,我明天就不在这里了,所以要抓紧时间。”疯子从桌子下抽出了一个布满脏痕的黄色箱子,放在桌子上,打开来。里面放着的是一本又一本的红色硬皮书,“你想听我写的哪一个故事?还是从最初开始听?”
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
“我们刚刚认识,从最初开始吧。从一切的最初开始。”我的背后窜起冷气,想要立马逃离这个废弃工厂。但是全身都僵住了。我扭头看了看年轻人,他还是斜靠在桌子上,冷漠地看着这一切。或许这是一个圈套,但我想不出为什么是我被他们困在这个地方。
“好的,一切最初的开始。我所写的故事,都是曾发生在这个工厂里的。”
我看了看他身上穿的那套破旧的格子衫,胸口处有一个模糊的菱形标志,由青紫两色构成。
“我想你是听过。对了,你的白大褂怎么那么脏,还有血迹?”他问。
我有些迷惑,看了眼身上,我所穿的只是我平常穿的白色衬衣,并不是什么白大褂。幻觉中的血确实还沾在上面。
“我不知道,或许有人往我的胸口刺了一刀。”我答。
显然,他对我的回答不是很在意。而是抽出了一本书来,开始阅读。
“2020 年 11 月 23 日,虚拟偶像组合 █-████ 官方账号在 B 站上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宣布组合正式出道。”
“什么?”
我脱口而出。
“我不知道。我在遗忘。”
没有主语的句子像无头僵尸一样在这个空洞的工厂内游荡。
“没有关系的,主语已经死亡。你要不要听下一个故事?”
我又点点头。好像我已经没有了别的任何选择,只是被一股强大的力推动着走。
“█-████出道至今,其实只有半年,这并非一段很长的时间,但由于故事开头过于低迷,过程又很跌宕,让人觉得仿佛已经过了很久。久到提起“████的狗”和“█门”这些红极一时的梗,都像是陈年旧事一般。”
他突然停了下来,向窗外张望着,像是在寻找些什么。
我感觉我的心疯狂跳着,但仍然僵在座位上。
“结……结局呢?”我问,声音有些发颤。
“结局是一天清晨,我在刷牙时再也看不清镜中我的脸——破碎的彩色碎片覆盖在上面,犹如面具。”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抽动,“在我注射针剂之前,我杀了一个人,在这里。匕首直刺对方心脏,血溅在面包上。”
# # #
在第四个世界中,人们终于能够一窥枝江,以及枝江市以外的世界的全貌。这时,枝江市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疲惫,迟缓而迷茫。
人们自从往裂隙之外的那一瞥后,就不由得对整个世界愈发失望了。他们本以为枝江市是一个极为无聊,而且干涸的荒原。但相比于外面的世界,枝江市似乎是这世上最后的尚存留有一丝活力的地方了。在水泥与水泥,阴霾与阴霾之间,还和这里一样,有无数个枝江市在漂浮着。但是那些枝江市中,没有水泥屋,没有和这里一样的从枝江市地底下打捞出来的那么多珍宝。
枝江市的众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他们从裂隙外目睹的,便是枝江市的未来。
枝江市逐渐走向停摆。一栋栋的写字楼升起,遮住了幼稚的水泥屋,文件从天空洒下,盖住了白色的森林。
有人说,这才是枝江市原本应有的样子。
# # #
整座工厂警报声大作,以至于需要我死死按住耳机,才能听到进入收容间检查的那人所对我说的那一番话,当时他正坐在那个巨大尸体旁边,几个月以来,这事已经在他心中泛不起一丝波澜。他的声音冷静而平淡,漫不经心地说出了那句在我一周后就与这一切一并遗忘掉的那一句话:
“毫无疑问,它们死了。”
它们死了。这是整个站点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随着警报声渐渐停止,我疲惫地倒在座椅上,看着我用了我半生研究的东西,在短短一年内灰飞烟灭,犹如一颗幻灭的明星,随之消亡的也有我毕生的心血——我的一切成果都变成了欧洲中世纪的魔法研究。
这个世界上一切传说中的永生之物都已不复存在,传说也永远成为了传说。那些从幻想中走出来的生物,最后都会归于他们原本来的地方——熵与虚无。
我走出研究室,白色的走廊上空无一人。这不是因为警报之类,而是大多数人随着它们的消亡都早已经放弃再在这上面花多大的心血,对一声又一声的警报更是无感,更何况现在正是中午饭点。我看着这洁白的墙壁,好像我一直都在做一个犹如地摊上廉价惊险幻想小说的梦而已,现在梦醒了,每一个人都只能在残酷的现实中被放逐。有人自杀,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卫生间中的血早已擦干净,用于割腕的剃须刀也装进了透明袋中,尸体也躺在停尸阁里,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自杀无非是一种将痛苦无限延续下去的方式罢了,而非终结。生活还要继续,即使每天的时间都变成了难以下咽的苦药片。静静等着上面的发话吧。在这种大变革下,我,和我相像的无数人对于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愈发显得可笑,只是随波逐流,等待着下一个我即将被冲到的河滩。
“走吧,别想了,都是必然。午饭时间。”有人拍拍我的肩。我没有回头去看那是谁,只是走着。这座被伪装为工厂的站点中,人群渐渐熙攘了起来,大部分都吃完午饭了。
食堂里,人都空了大半,少部分的人还没走,其中大部分都是和我一样的,还在等待转机的人。
午饭很简单,一根可颂,一根香肠,恐怕是随着它们的消失,上面资金也调不动了。我打好饭之后,和往常一样走到我常坐的位置上去。十三,左转四。我的对面是一个看起来比我年龄稍小点的员工。他身上脏兮兮的,看样子有几天没洗过澡了,头发纠结在一起,胡子肆意长着。
午饭寂静,我们两个人本互不认识,也从未在同一个工作项目上共事过,自然是没有什么可聊的。
他吃完,用口袋里自己的纸巾擦擦嘴,瞟了一眼我,然后说:“喂,你觉得他们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废人。”
我愣了半晌盯着他看了一眼。
“不知道。”我耸耸肩,“你知道吗,这个站点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了,我刚刚送走最后一个。”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然后凑到耳边和我说:“这没什么意思,一年前就开始了,但是谁注意了呢?重要的是我们将何去何从。我听说上面那群人想记忆删除了我们然后再打发走。到时候,伪装成工厂倒闭就行了,而我们也将只是一些社会上的游民而已,你也知道,现在厂子倒闭很多,下岗潮呢!”
听他如此说,我略有鄙视:“现在这种特殊时期嘛,阴谋论海了去了,别太信。”
“生活就是一坨狗屎,你知道吗。有些时候连屎都不如。”他端起餐盘,就要离去,“毕竟,屎有一天也会自然解构,但是生活,它就在那,交给时间没有任何用。它只是从我们出生到老一直纠缠下去。”
我点点头。
他很安静,把粘上油渍的擦嘴纸扔到盘子里,起身,离开,没有回头看我,哪怕一下,只是径直端着餐盘走了出去。
我也快速解决掉我面前的这一堆东西。而后也走出食堂。
这座北方的小城——枝江市——显出一副病态的模样,无数座工厂曾拔地而起,高昂地奏响工业浪潮之歌,随后面临的却是几十年后的大规模倒闭破产,给后代留下一座座破败的工厂遗骸和漫天的尘霾,以及那些似冰冷,却仍泛着炽热的粗糙而光明的铁水一般的历史记忆。当然,如果上头放弃任何转型的话,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和我工作了数十年的这处胜似家一般的地方,也会成为一处历史遗忘的一隅。我快步走回这座建筑内部。
“请本站点内的所有人员不要惊慌,从去年开始,我们便观察到了异常情况的显著增多,直至前五分钟,我们确认并报告了Z类情况的出现。所有人员请在两点半之前来到A栋建筑二层的大会议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很抱歉占用各位的午休时间。再重复一遍……”
广播内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在站点内回放。我叹了口气。看来一切都将结束。
我突然想到了食堂里的那个员工,如果真的要执行大规模记忆删除的话,我还从没想过任何职业转型的问题。
站点楼梯间中人流的流向已经很明显了,一并向二层涌去。我也投身入人海,去参加这场讨论本没什么好讨论的问题的紧急会议。
会议室内窗帘紧闭,但遮不住正午的阳光。阳光将米黄色的窗帘晕染得更为朦胧。进来的一些人面色都略显颓废与疲惫。有几个人甚至已经换上了便装,就等着通告立马解散。我白色的实验服还没来得及换,上面显出的些许灰色在这个不算昏暗的环境下依然有些显眼。油污静静地带着微笑站在上面。站点主管坐在台上的长长的桌子前,穿着黑色西服,但是中年后发福的身体把西服有些撑开,失掉了美感,谁知道这身衣服是他什么时候买的呢。我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一只在我坐的桌子的边缘上爬行的一只小昆虫身上。它的轨迹稍显弯曲,随时等着下一秒被人碾死。
主管清清嗓子,和往常一样形式上示意安静,尽管会议室中本就鸦雀无声。
(针刺入了皮肤。)
“我们的主旨是....,但是在今天,情况彻底改变了。在座的各位,详细情况肯定大家都知道了,至于各位提出的不同假说,诸如模因污染一类,我稍后会向大家作以解答,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该何去何从……
(药剂浑浊。)
“……监督者议会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的扩展面广,招募人员多,同时Z类情况的突然出现也使得我们缺失了在机构中的信任度,资金来源也出现短缺。总而言之,我们从今往后很难在建立下去了,上头最后给出的方案是,解散。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这里是每一个人,包括我,曾花下无数心血的地方,以及我们间的同事情,友情,甚至一些人在这里找到了另一半……
(注入,略有疼痛。)
“……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我们所进行的操作是完全可控的,所以不必担心一些关于生活至关重要的记忆被……
(失忆的白色。)
“……我知道。请你坐下,先生麻烦请你坐下。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记忆删除剂的药盒掉在地上。)
我在黑暗中醒来,一定是喝了太多白兰地,嗓子火辣,胃中一片翻涌。我试着从桌子上爬起,但是却被涌上来的呕吐物逼得又把头埋下去,最后沥沥地在地上瘫了一片。
这是在站点的最后几个夜晚,告别晚会像一列直逼凌晨的列车。就算如此,我恐怕喝得实在太多了,没有戴手表,但也可以估摸着时间是要往四点走了。我用袖子狼狈地擦了擦嘴,站起身来,眼睛逐渐适应黑暗,灰色的桌椅轮廓被勾勒出来。我看着这场狂欢后的一地狼藉——很明显这里之前是食堂,但是桌子中间的桌子移出了一片空地,供人跳舞之类的。地上有着被踩脏的彩带,零散地就在这里散落着。食堂餐桌上的一些盘子里还放着可颂与小饼干,大概甜点一类。有酒,有破碎的酒瓶。如果我没有这么狼狈地醉酒到这么晚,恐怕能够听到结束后人们稀稀拉拉地走出食堂的疲软的脚步声,以及同样稀稀拉拉地哭泣。没有尸体,还好没有发展成一场自杀派对。
或许食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扶着桌子走了两圈后,终于又清醒了些。我踉踉跄跄地往食堂门口走去。十三,左转四。桌子上有一团缩起来的黑影。我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在黑影对面坐下。他很明显是注意到了我,抬起头来。
“主管说了啥,你都听到了。”
我认出了,是上午坐在我对面吃饭的那人。
“嗯。”我点点头,“你是对的。”
他什么也没有说,又趴了下去。
“那我走?”我问。
没有回答。
于是我自顾着起了身,摇摇晃晃向门口走去。越往前走,越觉得黑夜是如此明亮,如此耀眼。华北平原无限延展,枝江市也随着无限延展,然后一齐投入这黑夜之火中。仿佛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永恒光明。我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看那个人,他已经融入了食堂的黑暗之中。我驻足。然后又往回走。如果记忆是故事,虽然它有一天会被投入焚书堆,但是,无论如何,结尾应该是明亮的,应该是明亮如黑夜的,而非结尾草草,成了一只腐烂在食堂内的老鼠尸骸。我不认识他,但是我想和他一起在黑夜下安眠,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出来吧,黑夜在燃烧呢!”我大喊。
仍然寂静。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他从实验袍中抽出了一把匕首,而他的旁边放着一瓶白酒,没瓶塞。刀刃反光,一瞬。然后照他的手腕切了下去。哦,是自杀。我的心中在那一刻没有任何波澜。然后他把白酒往自己手腕上浇了半瓶,剩下半瓶则一饮而尽。我没看到血,太黑。
哦,是自杀。我把这话又在心中重念了一遍。是自杀。
我跑过去,想要夺下他的刀,虽然我知道他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他的紧攥着刀柄,嘴中嘟囔了些什么,但我没听清。然后他把刀刺入了我的胸口,毫无缘由。我们一起摔落在地板上,我的头还在食堂的椅子上磕了一下。毫无缘由,我又重复了一遍,毫无缘由。然后血溅在面包上。
实际上那一晚,黑夜就已经将枝江市烧得干干净净,剩下的都只是残留下来的余烬而已。
第二天,食堂里没有发现尸体。
# # #
第五个世界,或是第六个世界。一层又一层的世界迭代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每一个迭代都像是前一个迭代的完美复制品,早已没有了任何继续观察的意义。
枝江市的故事没有意义。
# # #
“这就是结尾。从那天起我疯了,我再也分辨不出自己的面容。太模糊,你明白吗,太——模——糊——”疯子说。
手电筒安然地放在我的手里,而我已经将它关掉。在这黑暗中,我确实看不清他的脸。
“很好的故事。但是就这样,戛然而止?”我问。
“就是这样。因为第二天这里就解散了,再也不复存在了,而我们的记忆也都被选择性地抹去了。所以故事再也没有后文了。”
“好。”我说,“睡觉吧。我还要守着这个厂子。”
他没有回话。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疯的吗?”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我有些发愣,然后摇摇头,但是不清楚在这黑暗中能否看到我的动作。于是我又说:“你知道你有些疯?疯子们大多可不会这样觉得诶。”
“我本来没有疯,只是我的记忆前后矛盾了。”
“怎么矛盾?”我看了眼手表,夜光的指针幽幽发出绿光。大概快凌晨两点了。
“因为我的记忆,他们一定少删除了一些,所以我还记得那些事,那些你们都遗忘了的事。”他把一本书放在我的面前。我看了看,却发现里面都是空白页,“想起来了吗?你看你,身上还穿着这一身制服,胸口的血十多年都没能干掉。想起来了吗。”
臆想,我想。我又摇摇头。沉默是否定的。
“那我再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这座工厂无关,而是关于整个枝江市的。”
我点点头。沉默又成肯定的。
他叹了一口气,说:“‘第一个世界里,枝江市建成不久,从东走到西只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神还很小,他创造出的世界还存留有一点点活力。然后枝江市开始迭代,迎来了第二个世界。‘第二个世界里,枝江市开始延展,一条河流从西流到了东,在星河下的虚空无尽坠落。人们挖开了柔软的,似大脑褶皱般的土壤,发现他们的世界不过是建立在一片凝固着的灰色的大海上……’第二个世界里,枝江市迎来了黄金时代,也是这一切最为活跃的时候,这座工厂人来人往,或者,那时它还不是工厂,你可以叫它‘█圈’。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下的。我很难描述那个神,你可以把他视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实体,但是有着形而上的意味。枝江市的兴衰,根本上都是神的意识,潜意识与前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的结果,于是,随着神意识观念的改变,枝江市进入了第三个世界。"第三个世界中,枝江市已经无限延展,直抵世界的边缘……先是有一天,人们打开了一座水泥屋的门,发现里面涌出的都是意识海的那冰冷的灰色海水……"我们的这座城市,枝江市,在第三个迭代中便开始衰颓,而后很快就进入了第四个迭代。在第四个世界,█圈成为了一具冰冷的骸骨,倒在枝江市的郊外。而后的第五个世界,第六个世界,情况没有一丁点的改变,只是越来越糟。按理说,你我都是前几个迭代的产物,但是我留在了过去,却还要不停地牵扯着往未来走。”
我愣了一下,疯子嘴中的这一串文字长城让我有些发懵。
“对啊,枝江市在变啊。这是时代的更迭,从上世纪的工业浪潮开始,到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工厂倒闭。这就是时代。”
“时代……我们脑中,观念的改变,也是时代更迭吗?”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
“好,那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们都只是活在神的脑中。但是神疲惫了,神遗忘了,他忘掉了那些奇怪的歌曲和写满字的破纸,他忘掉了。明明这座工厂内的一切都是他的天下,包括我们也都是!他忘掉了!你明白吗,他忘掉了!他忘掉了我们的过去,但是我的却仍有残留,这正是我疯癫的原因。”
“哦,这你这么说那个神的记性不太好?”
“不是记性,而是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不了我们自己了。我们确实还是曾经的那个人,但是背景,职业,一并被篡改扭曲了。在故事的最后,我杀了一个人,对吧。哦,准确来说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你。”
这一切反常得让我听不下去。
“你是说我们活在故事里?”我问,“那我为什么没有死掉,你也是。”
“因为神只给我们设计了我杀死你这个情节,但再无后文了。再无后文。原本我记得我已经杀死了你,但是你又出现在这里,所以我疯了。我明明记得我已经割腕自杀,但是却从未真正死去。本身这就是一个迷,我没有理由杀死你,但是无论如何那把刀都会刺入你的胸口。”
疯子从肮脏的实验袍里拔出了匕首,向自己右手手腕割去。黑暗中我看不清血,但是能看清匕首那一瞬的闪光。血很快就干掉,他死不成的,我想。然后他把刀刺进了我的胸口,我倒了下去,头磕在食堂的冰冷的椅子上,身子则压在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上。我勉强看去,那是两具尸体。大概是我和疯子的,我猜。可能我也有点发疯了。
█圈已经被解构,化为乌有。幻想之物已死,只剩下冰冷的工厂。
那是现实。
# # #
不知道是第几个世界里,枝江市仍然很有活力。通向大海的井被填平,水泥屋一座又一座倒塌。在最后一座水泥屋倒塌的前几秒,从其中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失意落魄的小说家,一个是困在前几个枝江市迭代中的疯子。他们摇摇晃晃,互相搀扶,血不住地从他们身上的伤口上流出。
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白色的森林,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最初。他们走到林中。树木密密匝匝,遮住了正午的紫色的太阳,剩下的只有黑暗,白色的树干与层积起来的淡白的落叶被晕染成灰色。再往内走,树木便开始发出淡淡的白色荧光,乳白色的雾气也渐渐升起。他们停下了脚步,抬起头望着参天的巨树。在他们上空,漂浮着无数具死尸。那是意识海中无数幻想之物的一个集合。千奇百怪的种种作品以及它们所衍生出来的一切,所谓的尸体。它们缓慢而平静地漂浮着,像是漂浮在大兴安岭的一条河流上。他们在空中静静地分解成了雾,成了意识海里的水。
他们缓慢地行走着,最终走出了这片白色森林,森林的尽头便是大海。那时已是黄昏。在紫色的太阳收起最后一缕光芒之前,疯子蹲在沙滩上,缓缓地玩起洁白的沙子。尔后,一切归于平静,太阳落山,世界陷入了微明的紫色,非明非暗。大海在蒸腾,褪去了一切色彩。巨大的蒸汽萦绕在他们中央,但没有半点热气。等到雾气散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银白色的巨谷。
于是,作家拉着疯子,一起跃入了这银白的,空洞的大海。
片尾曲:
好多人接二连三地退坑,他们脱下痛衫,转而去与生活作斗争,但那些作品就摆在那里,供后辈欣赏学习,即使我们的笔停止划动,这些故事也必将永续且不息地流传下去。而若干年后的读者在读到这篇故事之后,将会为我们创作的努力和迷茫洒下一滴热泪。
瓶颈期的屑作,写起来或多或少有点无力感。大家看个乐子就行,但愿能活。
感谢每一个在精神上给予我支持的人,没有你们,我将堕落,毋庸置疑。
这篇文章是一份对未来的迷茫与忧思,这份忧思分为两份,一份献给我自己,一份献给整个社群。同时,它也是一份对我之前创作的总结,希望我以后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吧,但愿。
愿屏幕前的你能读完我的这篇一万字的烂文,也希望你能听完那首100 Years Of Choke。
祝好。
豆瓣作者:@黑尔戈兰岛


![全球微动态丨[原神] 画师Lumi合集 第二弹](http://www.cnmyjj.cn/uploadfile/2022/0610/20220610113604867.jpg)





![当前滚动:[龙王的工作] 空银子 优质图片](http://img.haixiafeng.com.cn/2022/0610/20220610014634425.jpg)